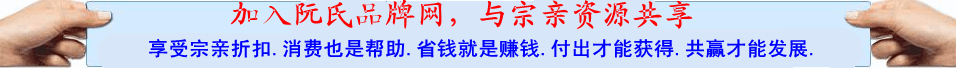善男信女
每晚跑步的路旁都有一位算命看相的大妈,携了几把塑料板凳,前面铺了一张乾坤八卦图,大妈就坐在那,等着善男信女前来咨询。每次我都从大妈的摊前跑过,不敢放慢脚步去窃听她与善男信女之间的谈话;昨晚我注意到了大妈戴了一副镍色边框的眼镜,十有八九是老花镜吧!那是在我折回跑的时候注意到的。大妈摆摊的地方不算繁华路段,甚至有点凄凉,路过的人大多是上下班的工人,偶尔会有那么一两对牵手路过的情侣,或许这些情侣会对大妈的算命看相颇感兴趣,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想去偷窥下他们的未来,可能会坐下来叫大妈说点什么,我一直在迷惑为什么大妈不去繁华的路段,“造福”更多的人们呢?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想,因为我只是匆匆跑过。之前周末去逛街的时候,也曾在街边看到过一个算命看相的,这是一位年纪约莫在50到60之间的男子,我一下子不知道该给他一个什么称呼,说他是老人家,可是他却精神抖擞,双目烁 明,俨然不像老人家,说他是大爷又更觉得不妥,这世道,叫大爷都很别扭,去你大爷的;就如我每次去餐馆里吃饭一样,冷不防叫服务员一声“小姐”,硬生生地把自己当成了嫖客;所以我一般都叫美女,叫者顺口,听者也舒坦;这也像别人叫我帅哥或是靓仔一般,虽然知道这是大众称呼,但是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应该配这样的称呼,人呀!归根结底是复杂的动物。我姑且叫他算命的男子吧!那位算命的男子有自己的号,叫“黄大仙”,因为黄大仙也像算命大妈一样,前面铺了一张乾坤八卦图,顺着旁边还有一小段自我简介,只是“黄大仙”三个字赫然入目,这让我很是诧异,光天化日之下,称自己是“仙人”的真是有点胆大了。不过黄大仙的形象如果不是前面那副八卦图,我真的以为是某某艺术家在体验市井生活而故意沦落街头,黄大仙一把山羊胡须,头上留着刘欢的发型,尽显艺术家气质,黄大仙的生意还可以,因为他的业务范围更大,不仅算命看相,还攘括点痣、化灾等等相关业务。灯红酒绿的夜景,匆匆而过的行人,不知道“黄大仙”的眼里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是阿弥陀佛还是善战?
我的母亲也是个虔诚的信徒,属于善男信女的一份子。我大抵是不会去抵触她的那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那份她寄托了希望的信仰,我觉得颠覆一个人的信仰是不道德的,当然,这份信仰必须是正确的,佛教之所以能盛行几千年而不断香火,必有他的存在意义,这种超脱意识存在的超意识形态,我是默认的。甚至母亲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每逢初一十五就让我向伟大的各路菩萨上几柱香,再虔诚的作几个揖;起初,我是很不情愿的,总是敷衍着完成任务,作揖的时候也只是象征性的双手抱拳,挥几下而已,连腰都不会弯。后来,我慢慢地认识到,这是母亲赖以生存的寄托,我必须去尊重她所尊重的信仰。母亲还会花上那么点钱,去街上觅寻与神有私交的算命先生,给我算上几卦,算命先生说的好,母亲当然信以为真,说的不好,母亲就耿耿于怀,然后挣扎着去极力否认,有时也会向算命先生讨教破解秘方,这种有点自欺欺人的模样就如我们总是在感情逝去之后,嘴里嘀咕的缘分一般,缘分的存在就如菩萨的存在一般,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宿命论。
我不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彻底的虔诚信徒,我只是有时信,但是我从来不迷。从小至大,我也跟着母亲拜过很多菩萨,后来长大了自己出游的时候遇到庙宇佛像啥的,也会拜拜,但是我从来不会慷慨的往功德箱里面塞钱,因为我很难想象晚上寺庙“打烊”的时候,众和尚打开功德箱点钞的模样,我欲献给佛祖的钱,却被这群秃驴瓜分,很难接受。信仰,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我相信佛祖从来不会因为你上的香没有旁边人上的香粗而偏袒别人,佛祖讲究普度众生,福泽天下。
现在的我,准确的来说是有点相信“宿命”这个词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很多发生的事情,找不到任何社会规律去解释,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去诠释事态的猝不及防。于是我慢慢地潜意识里在接受“宿命”的安排,但是这不是消极面对人生,而是一种在你感到无助、无奈、无望的时候用来解脱自己的最好辩证法。
萧敬腾有首歌就叫《善男信女》,歌词里这么唱到:祝福什么都不再记住,祝福下一次总会幸福,祝福爱情的信徒,那善男信女别太辛苦。或许我不是宗教虔诚的信徒,但是我是一个爱情的信徒,绝对可以用虔诚来形容。我用“宿命”一词去等待下一次幸福,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去找那位大妈和黄大仙给我指点一二,听听善男信女们怎么看这红尘喧嚣的世界,以及我那还未出现的“宿命”。
席慕容诗中写道: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於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我愿做你虔诚的信徒,爱情永久的情人,当然,还要做一辈子物质的走狗。
2013年10月24日 阮荣
{:1_14:}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