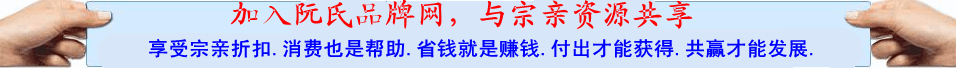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阮若珊
阮若珊,阮慕韩长女,1921年4月25日生,祖籍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幼年在家乡小学读书。1933年随父母迁居北平,1934年在北平师大第二附小毕业,由学校保送至北平师大女附中读书。1935年冬参加了北平“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2月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队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生平简介
1937年初中毕业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为躲避敌伪统治下的学校,便于开展“民先”地下工作,她转入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学习。1938年夏秋之际,因北平地下“民先”组织遭破坏,组织决定她离校去天津,后由天津地下党组织护送至晋南抗日根据地行政主任公署并同时加入八路军129师。1939年春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同年秋毕业分配至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任演员,同年10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冬抗大一分校文工团随抗大一分校校部从太行山东迁至沂蒙山区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此后7年一直在沂蒙山区,在山东分局及115 师师部领导下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工作。此间她作为文工团的主要演员之一,除参加多幕话剧《李秀成之死》、《阿Q 正传》等演出外,特别是在小调剧《亲家母顶嘴》、《抗属真光荣》、《双喜临门》及抗战胜利前夕动员参军的独幕话剧《过关》等剧,她扮演的农村大嫂、妇救会长等角色获得观众的喜爱。在此期间她曾创作小话剧《一双鞋》、《彭大娘》等小型文艺作品。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在蒙山望海楼山下费县白石屋村,她和文工团的另一位成员李林同志共同创作的《沂蒙山小调》成为著名的革命历史歌曲。
1945年抗战胜利后,阮若珊离开沂蒙山区,苏 115师肖华主任及大众日报的同志渡海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此时任辽东军区文工团教导员兼作演员,参加了大型话剧《李闯王》(演红娘子)及《气壮山河》(演女特务)等剧及节目的演出,在部队慰问演出中获得好评。 1949年全国解放后,她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至武汉,任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后为中南军区文艺工作团“战士话剧团”团长。在此间除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参加了《战斗里成长》、《曙光照耀莫斯科》等剧中角色的塑造工作,并创作了舞剧《母亲在召唤》;1954年调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任团长。组织演出了《杨根思》等剧目,培养了李传弟、陶玉玲等大批优秀演员。
1958年从部队转业至中央戏剧学院,历任导演教师、系负责人、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培养了一批从事表导演的学生;1986年离休后,参加了《欧阳予倩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编辑工作,分别为编委之一,并撰写了《在战斗中成长》等回忆文章和散文。
她一生为部队文化建设、培养戏剧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2001年11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代表作品
《沂蒙山小调》诞生于抗战时期的1940年。当时抗大一分校由蒙阴县的垛庄一带迁驻费北,该校的文工团就住在下白石屋村。为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打击当地的反动地方武装组织“黄沙会”,他们创作了民歌《反对黄沙会》。由阮若珊(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作词,团员李林(现为上海歌剧院顾问)谱曲,后来经过不断地修改加工,便成了今天传唱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沂蒙山小调》。
1999年,费县委、县政府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建立了纪念碑、纪念亭,记载了《沂蒙山小调》诞生的过程,以及现今流传的《沂蒙山小调》词曲及作者,以启后人,永志不忘。并请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团长、国家农业机械部副部长袁成隆同志题写了“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纪念碑名,词作者阮若珊同志题写了“深深怀念沂蒙好地方”,分别镌刻在白石屋村旁的巨形花岗石上。
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黄宗江给阮若珊的万言情书(节选)
阮若珊同志:写这封信的今天,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您女儿们的节日。你再也想不到远在太湖会有一个你只见过他一面,他见过你两面的人——也许这一面您都毫无记忆——他遥想北京城,给你写下这样一封“情书”性质的信!……我们都是三十好几,踏过半生的人,半路杀出这么一位中年突击手,面对面实在有些窘迫。我既难卖老,也难充小,我对“年轻人到底是怎样谈恋爱的”实在有些惶恐生疏之感了(这是一种实在的感觉,但不完全是实话),那么我首先希望没有吓着你,或者已经叫你生气;至少希望起码的好奇心能使你静静地读完我这封信,看看这个家伙到底能说出什么道理。真情给予我勇气!
我第一次听到“阮若珊”,是在1953年冬,嗣后的岁月里,我又偶或道听途闻,掇拾了一些人物片段……何以就记住了“阮若珊”请允许我用个唯心的,却的确是可喜的字眼“缘分”吧。
五年来,我过去的妻子几乎在用精神分析法和我做感情的“谈判”,我的感情处于一种破碎、麻痹、混乱、绝望的状态。虽然有名无实,我总是个有妇之夫,道德的羁绊也不容我对刚才所说的那些微妙的感情波纹多作幻想。前不久,她终于寄来离婚报告,我签署寄回,组织上批准了这实质上已几乎五年的离婚。我又成为一个无妻无后了无牵挂的人。留得半壁青春,对生活比过去戒心重重,对周围的姑娘们不由得不产生一种犬儒式的不能信赖的心情……我倒的确还不是一个热锅蚂蚁似的急于求偶者,我需要面壁休整。但是,不知何来“远山”仙风吹拂荒原,萌芽状态的生命的召唤在不知什么时候茁长起来,茁长得那样意外地强烈,迅速,而又隐密;隐密得只有爱情才要求那样的隐密。隐密得不想告诉第三个人。(除非这第三个人是千古侠肠的红娘!)
你会谦逊地说,你有不少缺点,我不知道。那当然可能,我也预备对您做“个人崇拜”。我对您的理解也难免概念化,但我相信这概念的正确。我说您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女人。
我说你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现在很多女性不愿接受这种“软弱”的赞辞,她们甚至以为这是一种贬辞,但这是马克思说的———温柔是女人最崇高的品质。
我说你一定是一个工作上,戏剧事业上很好的战友,我看见过你在剧场里那种带着困惑目光的孩子气的微笑,那样的人,才是深爱剧场的人。我寻找那样的人。近二十年剧场内外生涯使我养成一种养马人似的习惯,不论对场上奔驰的,或是静静伏枥的马,我总要打量一下鬃毛、牙口……在这方面我常常是神往的,但又是极苛刻的,决不随便同意乱发三等奖。在“爱才”方面我还残余着一定的唯心观点,但是看得准的时候也还居多。你作为一个演员或导演,在台下给我的印象并不“光彩夺目”……但我们看过不少过眼云烟,光彩的凋落,我相信你是能老老实实地灌溉一株“冬青”的人。总之,朋友,我愿在剧场里陪你坐到深夜,我们能找到共同的潜台词的。
你当然是个好母亲。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过分娇宠了失去父亲的孩子?一天,我的妹妹宗英和妹夫要帮我规划“未来”,我笑着说我要娶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和我血肉相连的小妹,一听就懂大哥不是无所指。她自己是两个孩子的后母,她说:“做后父也不比做后母容易啊!”她瞟了一下妹夫说:“不过你那时要没有一双儿女,我还不嫁给你!”冷场片刻,又望着我说,“这大概所以你是我的哥哥……”关于这一点,不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若珊同志,你是一个应该有美满家庭而没有的人,我多希望你和女儿们能幸福啊!假使我想把我的幸福和你们的联在一起,这不会是一种自私的愿望吧……若珊同志,你愿意和我合写一本小说吗?请原谅我没征求你的同意,就开始写小说的序言了……我再一次要求你理解我:我是幻想,但我并未脱离现实;我是在猛冲,但我并非盲动;我出发得异常地慎重,因为这一切关系着我后半生的生活道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六月之夜。
本帖最后由 阮礼军 于 2012-7-26 16:34 编辑
巾帼须眉,阮门骄女{:soso_e179:} {:soso_e163:} {:soso_e179:} 我们阮氏家族的自豪 {:soso_e179:} {:1_14:}
页:
[1]
2